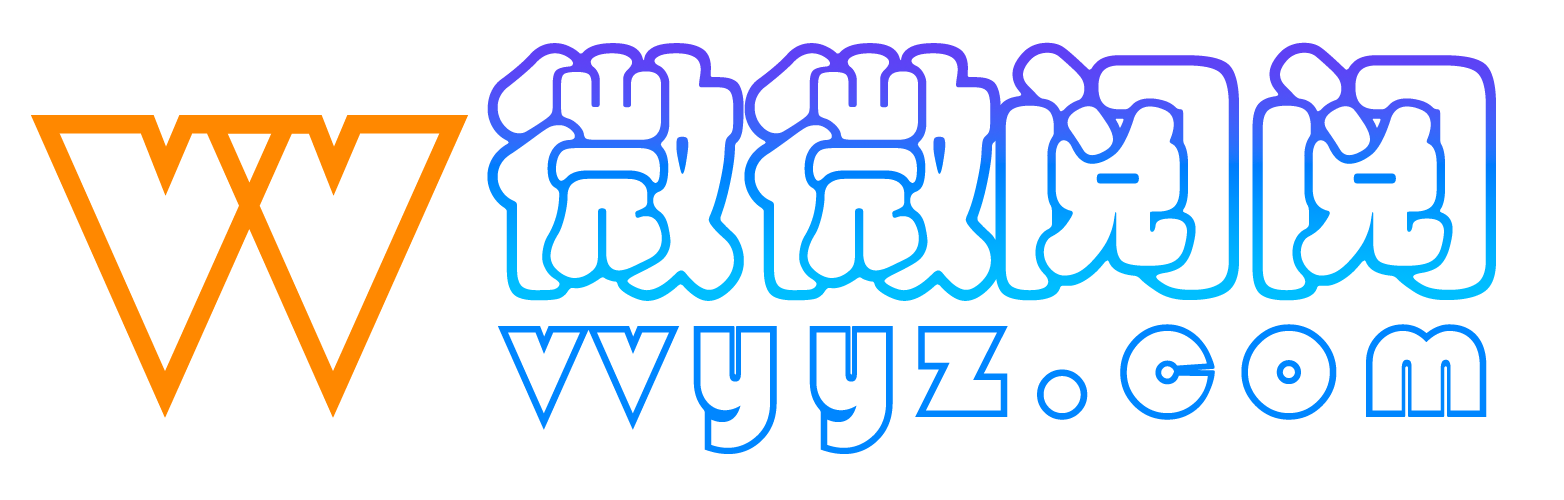
我爹爹和禁卫军他好友张河里应外合逼宫。
事成之后,爹爹带军退出午门时被突然冒出的士兵射杀。
兄长见此,悲吼一声,拔刀反抗,刀尖还未出鞘就被千百支玄铁的飞羽箭射穿,全身下上皮肉没一处是好的。
娘亲和***抱着未满百岁的侄儿在家中忐忑不安的等着爹爹与兄长的归来,哪知等来的却是太子贴身宦官亲手绞杀。
而我、在太子府。
一杯太子赐下的鸩酒,他最得力手下旬风站高处冷眼看我狼狈含泪饮下。
曾经无限风光的太子妃也不过是草席一张,扔于乱葬岗。
.天阴涔涔地,我从死人堆里爬了起来,满身尸水混合的淤泥。
摇摇晃晃站稳,抬头望着阴暗地苍天,嗤笑一声:老天都让我回来,司马瑯,我姜家血债必让你用骨血偿还!
靠着复仇的执念,拖着强弩之末的身体踏上官道第一步,再也撑不住晕了过去。
梦到少年,那时父母的纵容,让我学会了弓箭,学会了骑马。
和其他的千金不一样的肆意洒脱。
别人说上一两句的时候,父亲总是说:「我家的囡囡是自由的雏鹰,只要我这只老鹰在一天,便会让她自由在天空翱翔一天。」
梦到意气风发稚气未退的兄长拉着我往前跑,阳光正好柳枝冒着嫩芽春风拂面。
他朗声道:「走,烟漓,哥哥带你去赛马。」
梦到我穿着华服哭着拉着衣角求父亲和兄长:「爹爹、哥哥,求求你们了。
只要成功,爹爹还有兄长以后就再也不用去上战场了,琅答应过我。」
梦到他们无奈答应后,侍女扶着满脸高兴的我跨过将军府大门刹那,天色急速暗下,脚下不知何时溢出如长河的鲜血。
再抬眼四周漆黑,只剩我一人孤零零站在那。
梦到金瓦赤墙下兄长满背染血的箭羽,父亲的头颅早已不见,母亲与***缢死在奉着满是姜家祖先的祠堂,未满百日的侄儿漂浮在***最爱的那盆荷花坛里。
。
。
。
。
。
猛的惊醒,心中不停翻腾,喉咙里冒着腥甜。
「咳!
」一口鲜血喷出,在暗色金丝的被褥上再染深几分。
司马厘慌忙把我扶起。
剑眉入鬓,俊眉朗目,和司马瑯有几分相似。
待我瞧清后,倏然把他推开:「滚。」
司马家的人都让我犯恶心。
兄长与他和司马瑯是少年相识。
踏春那***们约好去看桃花。
由于平日过于的肆意,娘亲让刘妈妈亲自看着我学习绣艺。
学的百无聊赖,眼神与窗外清丽的梨花交汇几十回合。
外廊突然传来嘈杂声,一听就是兄长。
顿时来了精神,我双手撑起身子,向院子门望去,梨花簇影遮挡了大半视线只看得模模糊糊人影。
"哥哥......"「小姐!
」我兴奋地刚开口就被刘妈妈止住。
瞟了眼威严的刘妈妈我又坐了回去:「知道了。」
但还是被兄长听见,当着刘***面拉我出了门。
.三月春风带着微微寒意。
我穿着男装骑马跟着兄长与他们会合。
在一棵大榕树下看见了骑马的两人。
兄长扬手喊道:「瑯兄、厘兄!
」阳光斑驳,反射着树叶绿意盎然。
司马瑯一身赤衣胯下一匹毛色发亮的骏马,听见声音扯着缰绳转了个身笑道:「姜兄。」
鲜衣怒马,少年咧嘴一笑,眉眼中光点闪烁,比路边的野草还有生机。
当时脑袋空空,耳尖爬上红云,我眼中只剩司马瑯一人。
想着以后定要带他去我心中的塞外,看那浩瀚的星空。
而司马厘则在他身旁呆呆的盯着我,同样的红透了耳尖。
或许我当初选择的是司马厘会不会不是这个结果?司马厘安排我养伤的庄子离京城不远,快马加鞭大概一两个时辰就能到。
我躺在床上看着他安排的郎中进进出出,换了一批又一批,不变的是神色紧张的进来,跪地求饶的被拖出去。
唯有一郎中拱手说道:「公子,这鸩酒是奇毒无比,加之姑娘心力交瘁,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怕是熬不过月底,但........」他紧了紧手,满头大汗:「小人有一方可缓解其毒..........」不知道他说的只是为了保命还是真能救治我,所需要的药材皆是千金难求,还需要一人的心头血。
但也是我唯一的生机。
我只拉着司马厘苦苦哀求:「救我,我还不想死。」
大仇未报我怎么能死?活、我得活!
胸口一痛,口中一哽鲜血冒出。
司马厘紧紧地抱住我:「烟漓,我答应你,我答应你,我不会让你死的。」
我的手死死地拽住他的衣袍晕了过去。
往后几日少有清醒的时刻,就连替换口中吊命的参片也难将我弄醒。
偶尔醒来会听见丫鬟碎嘴:「也不知道这个姑娘是殿下什么人,让殿下这般费心费力。」
「可不是,听说派出去寻药的人都是殿下的暗卫,带着殿下的亲印去的。
今日听马厩的张叔说已经废了五六匹良驹了。」
「就连殿下.........」精神头支撑不了听完丫鬟们的碎嘴又晕睡了过去。
不多久药材聚齐,只差一味心头血。
至于缺的那味药引心头血,诏狱中的死囚那么多,我想也不难。
药丸制成后身体稍好些,我便彻夜的彻夜的睡不着,一闭上眼就是无尽的血色。
睁眼幽幽地看着窗外的明月,想着爹爹娘亲们。
忽地听见门扇轻微开合的动静响起。
我保持姿势不变,阖上了眼。
带有不一样药的味道靠近,但我终日在药罐中泡着,或许是闻错了。
那人站在床边看我良久,忽间眼皮传来凉意的触感,带着熟悉的味道。
是司马厘。
说起来从制药开始后就没有见过他了。
他用指腹轻抚我闭上的眼睛。
我眼皮控制不住的颤动。
.他曾经对我说过:「烟漓,你这双眼睛不适合待在宫中。」
那时的我不以为意。
宫墙只会成为弱者的阻挡。
只要司马瑯当了皇上,我当了皇后,他这么宠我,就算再深再高的宫墙那也是来去自如。
他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动作,轻笑一声,又用指腹轻轻地点了点我眼皮。
而后听见他压抑不住的轻咳,他撤回了手,转身走了出去。
我转头看着阖上的门,盯了许久。
又过了几日,身体恢复了力气,觉得是时候离开了。
「姜小姐,你当真要走?」司马厘的侍女雪月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我没回头,低头无言。
又觉得没有必要和她纠缠,正要抬脚,她又道出一句:「你知道你药引心头血是谁的吗?我转头望向她。
她扶着门框:「是殿下。」
「连着七日,他胸膛的伤口合了开、开了又合,只为你取那心头血。
姜小姐你还有点心就不应该离开他。」
眼中温热聚集,我以为我的眼泪早在那会流完:「姜家与司马家早在逼宫那日就不共戴天,我和他也.........」.......终是心中仅剩的良心无法让我再说后面的话。
无法说出***日夜夜的噩梦纠缠。
心中的仇恨就像一根荆棘从心脏长出,并自我缠绕,每跳动一下藤上的刺就扎进心脏一分。
也无法说出,因他姓司马,我姓姜。
雪月见我止言欲泣,妥协中又带恼怒:"殿下说马厩有你要的东西。
"她说完就甩手走。
「谢谢......」我木讷地看着她的背影道谢。
转身向马厩走去,那里有一匹早已备好的良驹。
马鞍旁挂着一包袱,里面有通关文书、一瓶药丸、一些银两以及一把匕首。
这把匕首我记得是他第一次猎下凶兽的奖赏。
那时司马厘拖着一身伤,站在我面前,眼里全是兴奋:「烟漓,给你!
」「我不要。
司马厘你是不是傻,这个是你第一次猎下凶兽的纪念,见证了你的勇敢和智慧,怎么能乱送人。」
我一脸怒其不争。
拒绝后这把匕首多次莫名其妙的出现在我的马车或者斜挂在马鞍上,但都被我好好的送了回去。
后来同司马瑯与他去游灯会,司马瑯送我一小摊贩上购买的银簪被我戴了好久。
手指摩擦了匕首好久后收好牵马向庄子外走去。
天悬明月,大地上的事物只剩一片剪影,孤寂得像是在梦中一样。
我翻身上马,扯了扯缰绳,看了眼京城的方向驾马而去。
.到城门口已到日出,遇上了一支车辇的队伍,浩浩荡荡的前往大古寺。
走在最前面的是南嘉的兄长南隽。
一身土***衣袍,胸前绣着麒麟,一张从眉骨划到嘴角刀痕的脸,满是煞气。
围观的百姓在议论纷纷:「今日是嘉妃父亲的忌日,怪不得要去大古寺。」
「听说她父亲之前百战百胜啊,如果活着的话肯定也是一位威猛的大将军…........」我站在人群看着奢华的马车,直到它变成一个黑点。
南嘉的父亲是中郎将。
原本与我父亲一样在前线冲锋陷阵。
但她父亲行事狠辣,生命与结果比更看重结果。
打仗时为了快速获取胜利,牺牲了不少百姓,名声不大好,文官参他的本如同下雪一样。
先皇便让他当了中郎将,守卫皇城。
也不知怎养出南嘉这样柔柔弱弱,知书达理的女子。
可能父母事不祸及儿女的缘故,加上南嘉待人礼数周全,时常乐善好施,与京城的各家千金关系不说甚好也有点头之交。
也就我和她走的近些。
冬季塞外战事吃紧,又快到元旦,我父亲旧伤复发正在家中养伤。
押送粮草的任务无人可接。
南嘉的父亲主动请缨接下此任。
那年的冬季尤其的冷,常下鹅毛大雪,道路十分凶险。
每次见到南嘉她都是一脸担忧愁,道路泥泞也常去城外的大古寺上香祈佛,只求她父亲平安。
在元旦的前一日还是传来的噩耗。
寒冷的冬季缺食物的不止是山中的凶兽,还有偏僻山村的百姓。
大雪一封,储粮也吃不上几日。
人在死的面前总是要搏一搏的。
队伍便受到了冲击。
南嘉的父亲当时受了伤却将粮草平安送达。
当时的伤虽不致死,但在快要回到京城时恶化病逝。
那日,我正和父亲母亲烤着暖炉,兄长带着消息从练武场回来。
隔日去南府,宅门已挂上白凌。
南嘉的母亲生她时难产而死,现在又没了父亲,现在这个家只有她和她兄长了。
南嘉抱着我一脸苍白,满脸泪痕像是溺水之人抓住了浮木:「烟漓、烟漓、我没有父亲了,没有父亲了。
。
。
。
。」
我紧紧的抱着她,轻抚她的背哄着:「没事的、南嘉,以后我的父亲母亲就是你的父亲母亲。」
由衷的希望她好受些。
那会儿塞外战事频发,死的大大小小称得上职位将领也有几十个,所以南嘉父亲的封赏迟迟未下来。
她兄长南隽只是一个小小百户,他们的父亲死后南隽更无背景,在军中处处受人欺凌。
也许是为了得势为了活的更有尊严些,南隽将他妹妹托与我家后随军去了塞外。
父亲母亲待她如同亲生女一样,连兄长时常带回来的新鲜物件有我的一份也有她的一份。
再见南隽时脸上多了一刀疤,疤痕还是刚脱痂后的粉色,眼里少了生气,走路轻微一瘸一拐,官职也成副骁骑参领。
来将军府接南嘉时偏执的向我父母磕了几个响头说:「以后定会犬马之报。」
如果让他去杀了司马瑯的话.........他不行,南嘉也不行,他们家只剩他俩相依为命了。
算了,我现如今孤身一人,死了也无人牵挂。
.只不过一两个月,将军府已是废墟。
书写着姜将军府四个大字的匾额斜挂着,摇摇欲坠,结满了蜘蛛网,门扇上贴了两张封条。
这个门见证了哥哥与我的大婚,无数的达官贵人跨过。